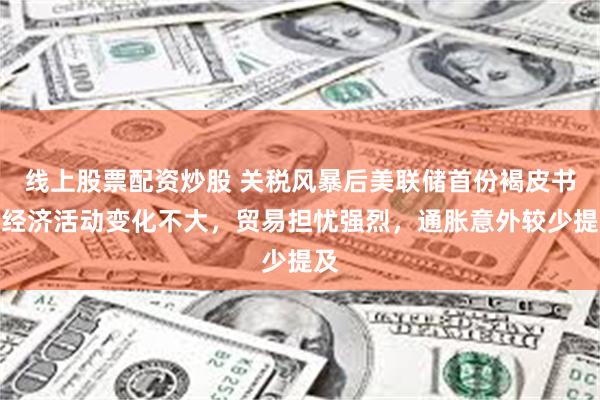股票配资要求 1790年代末期法国的通俗剧,包含了将家庭作为道德行为的规范_维克多_罗杰_塞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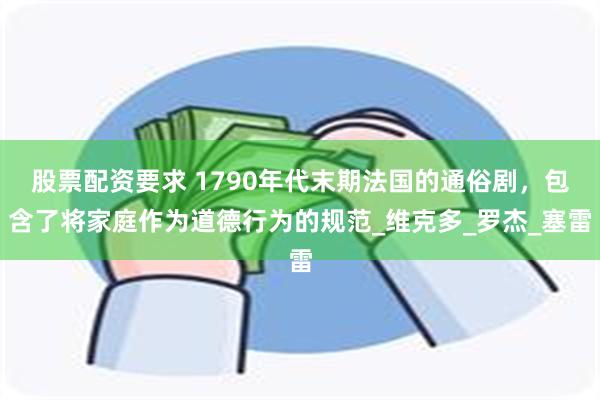
引言股票配资要求
1790年代末期法国的通俗剧,包含了将家庭作为道德行为的规范布鲁克斯及伯尔齐伯并不多加注意1795至1800年这段通俗剧成形的时间。在对早期的通俗剧达成精确结论之前,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但至少有证据显示,1790年代晚期的通俗剧,就如同小说一般,集中在特定的家庭罗曼史之上。
茱莉亚·伯尔齐伯在其大范围的研究《通俗剧工业》中挑战彼得·布鲁克斯对通俗剧的正面看法。虽然伯尔齐伯与布鲁克斯一样,都强调通俗剧在面临法国革命时期社会崩溃时的反应,然而她却将通俗剧称为“谬误的民主”:“我们的分析显示,通俗剧不至于反动却趋于保守的基础,赞扬奠基于家庭、宗教、社会阶级秩序而来的社会福祉,而反对革命的理念。”在结语中她写道:“通俗剧使得个人永远屈从于家庭、祖国、种族、阶级与人性。”
家庭的认同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而最后好人战胜恶人的关键,端赖于此“孩童”(通常是青年)是否能锻炼出属于自己的认同感。皮塞雷古本身的生涯展现出1790年代末期的社会、政治及相关艺术的不确定性。在孔代经历了反革命的军旅生活后,皮塞雷古返回法国,从事剧本写作。他尝试了所有主题均告失败,直到他借由改编自多明尼的故事而“发现”通俗剧。
展开剩余82%皮塞雷古改编《森林之子维克多》,甫一开场便让家庭罗曼史成为故事主轴。第一幕幕启时,维克多在“哥特式城堡”中散步,开场的独白显露出他的困境:是的,我必须怀着敬意离开此地。在这城堡里我受人抚育,在这花园里我接受无数次克莱明丝的拥抱,她视我如兄长,我却狂恋着她。我应该抛弃一切······是的,一切。但是,我的保护者······这位可敬而正直的男人,希望我能在他年迈时为他分忧解难,我怎有勇气弃他于不顾?
1795年后期的家庭罗曼史全然从小孩的角度来看事情:儿子抛弃养父、直到维克多解开认同之谜后方才纾解的可能性乱伦,对女儿慈悲的依赖,新男人融入世界所遭遇的难处······维克多自认为是“被遗弃在森林中的不幸小孩,没有双亲,没有朋友,举世无依”,他能够奢望成为日耳曼首屈一指的庄园主的女婿吗?除了结局的某些显著元素之外,此出通俗剧与小说相去无多。在小说中,弗利芝纳的庄园主与维克多的生父罗杰都在剧终时身亡。罗杰至死不愿悔改,但他也承认自己乃是将罪行“藏匿在最谬误且最危险的体系中”(在此或许暗指激进的革命)。
因为克莱明丝在统治的男爵前为维克多辩护,他因此在临刑前获救。如同1790年代末期的俄狄浦斯绘画主题,女性扮演了调停父子,或是调停男性与法律的关键角色。相对地,在皮塞雷古的通俗剧中,养父与生父在剧末均与维克多达成和解,家庭的调停成为主题,女性的角色则受到逃避忽略。当庄园主呼喊出维克多是他的小孩后,他在战场上从罗杰的强盗群与帝国的军队中间幸免于难,在罗杰身负重伤而奄奄一息之际,他要求见维克多最后一面。罗杰宣称庄园主才是唯一有资格的父亲,并求取维克多的原谅。
在通俗剧中,强盗是普遍的主题。席勒的《强盗》在1792年被改编为法国剧,多明尼与皮塞雷古均受到此剧卖座之影响。在皮塞雷古的藏书中包括一册席勒剧本的法译本。自从1792年后,强盗头子开始有了微妙的转型,这项转型与革命本身有关。拉·马尔德利艾尔将席勒剧中对社会的反叛营造成为罗宾汉式的侠情。换言之,罗杰从叛变者转型为爱国者。五年之后,皮塞雷古将罗杰描述为“失败的革命者”,罗杰则自认为是“人性的复仇者”。罗杰向维克多解释道:“我对人性的爱,使我为了弱者反抗粗鄙骄傲且欺压他人的富贵人家。”
维克多认为父亲有其“罪犯的野心”而反对父亲的叛变,因为这并不符合一般的法律程序。维克多在对叛变生父间的自然情爱与对法定监护者的后天之爱中举棋不定,而试图让罗杰许下宠爱其孙儿的承诺,借此诱使他返回法律正途。当帝国军队抵达,维克多的抗辩失败。在皮塞雷古的版本中,家庭关系是其剧情主轴。伴随着城堡布景、强盗人物与快节奏的戏剧性,这乃是一个关于在危机中重塑家庭关系的故事。维克多对两个父亲的感情,以及他与克莱明丝共创家庭的欲望,这般的家庭罗曼史正是推动情节的主力。
1790年代末期的通俗剧,并不只是如布鲁克斯所言,是一种在焦虑的后神圣世界中的道德再造。而还是将家庭作为道德行为的规范。如《森林之子维克多》般的通俗剧一再展演关于血缘、父子关系、乱伦、社会道德的焦虑与解决之道。这是一种反复呈现民主或反动的强迫症状?这是伯尔齐伯所说的“对父权家庭与阶层社会感到抱歉”的表现吗?我认为答案是“是”,也不是。维克多交给我们两个讯息:孩子必须独立,因为父亲偶而会犯错,而通俗剧中通常会强调尊重法律与喜爱家庭的必要性。
在维克多对生父及养父的爱,以及他对法律的尊重之中,你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指称的“对父亲的渴求”。更有甚者,通俗剧中强调“挽回的爱”的品质,包括当男爵呼唤维克多为子,拯救他免于一死;以及维克多企图说服生父爱家,借此挽回生父-这是小说中所没有的部分。不论是否饱经折磨或问题重重,家庭是这危险而不确定的世界中唯一的天堂。显然,母亲几乎不出现在这些故事中,父亲被发现、与孩子重新和解,但是母亲是缺席的,因为在故事一开始就牺牲了,母亲因而被排除在故事之外。
如同大众小说一般,1790年代的通俗剧借着带来社会提升的幻觉,以及下一代观众的成长,使得家庭罗曼史开始民主化。不论是女店员、主妇、学徒与绅士都能经历到因为无法清楚感知自我认同而带来的焦虑颤抖;而当观众发现,即便是森林中的弃婴都可以成为有用的公民、快乐的丈夫或妻子时,他们又满心欢喜地松了口气。维克多与父亲的和解得来不易。虽然通俗剧软化了大众小说中存在的棱角,将其剧种之模糊减低至同质性的表现,但它还是与革命年代的担忧与焦虑相符。借用吉拉德的说法,任何献祭仪式性的危机解决方式,都必须提醒参与者他们曾经经历过的恐惧与惊悚。
在1790年代晚期,通俗剧本身也开始朝着保守的方向转变。比较皮塞雷古对《柯琳娜》的改编,以及他早期对《森林之子维克多》的改编,可以看出转变十分明显。同样地,对于血缘的不确定是故事的核心,而年轻人的独立则同样是强调的重点。相对于18世纪的“好父亲”论述,迪福尔坚持,除非柯琳娜心甘情愿,否则自己不会强迫她委身下嫁(第一幕,第八景),而柯琳娜则扮演了一个让特律盖兰原形毕露的重要角色。当迪福尔发现柯琳娜不是自己的侄女时,他终究还是变成一个暴虐的父亲。
在《森林之子维克多》中邪恶更为明显,因为其中罗杰乃是个矛盾的背叛者角色。舞台的方向使观众在幕启时便看清了特律盖兰的邪恶意图,而故事则充满着明显的多愁善感。在1800年左右,通俗剧面临着某些状况。在拿破仑时期通俗剧被重新格式化,家务事、婚姻、父子之间的调和等问题解决了个人在世界上开创人生的焦虑。舞台指引了观众,有助于消除关于界定恶、过度的野心、辨不清罪恶的焦虑。在这种普遍的“舞台舒解”方式中,性别角色也或许有所转移。在1800年后的经典通俗剧中,受害者几乎都是女性,背叛者是男性;而知识的提供者则都是男性。性别角色非常清楚。
相反地,在1790年代的小说中,年轻男性既是受害者也是英雄,角色非常不确定,成功则有赖于个人的本性而定。在1790年代后期,为了消化及重铸革命的经验,必须进行大量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工作。在许多方面,如小说、绘画、雕刻、庆典、通俗剧,甚至法令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朝向新的政治模型的家庭重建的运动,在其中人们经历了社会解体的恐怖,而个人则可以借由认祖归宗,建立他或她在世界中的位置。父亲重振一家之主的形象,但只限于他们有意愿扮演养育者与指导者的新角色,而非被释放的暴君。女人自限在母职之中,但是这时的母职被赋予更高的价值,母亲究竟应该知道些什么,在此时仍未有定论。
结语
复兴意味着重建与重新塑造股票配资要求,而非表示回归以往。在父母的角色重新定位之际,儿童成为新社会的代表性角色。结果不尽然是自由主义的,就如同《克莱尔》中女主角的悲剧性命运所揭示的一般。但事情显然是不一样了,许多巨大的焦虑来源浮出台面,社会中的再重组成为前所未有的明显现象。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只使父亲的权力具体化,且在家庭与个人间建立了脆弱的、不稳定的、持续变动的均衡状态。在那当中,父亲被砍头的记忆还是栩栩如生。
发布于:天津市